我的女侠
2018-05-18 14:44:06 来源: 第一新闻网 评论:0 点击:60005
第一新闻网 评论:0 点击:60005
【以此文献给我的欢欢大宝贝 她待我温柔 吻我伤口 为我出头 照顾过我的感受】
作者:钱雪
她和风四娘一样,
吃最辣的菜,喝最烈的酒,骑最快的马。
她也和像燕七一样护短,逞能,
甚至有些外强中干。
当我怀念江湖的时候,就和她呆一会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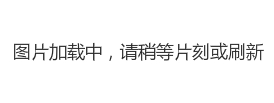
某一次,一位哥哥这么问我,
“雪儿,你是喜欢乖的还是坏的”
这位哥哥是略胖点的容长脸蛋儿,细柳柳的单眼皮上挂两道最淡的小山眉,人生得白而高,是实打实的白面儿砌成的。
很有唐代书画人物气。
然而他这个人却又是很现代的,被几年西方生活锤炼过,整个人浴火一样非常崭新,抽最新鲜的烟,有最开明的思想。
“喜欢乖的”虽然这样说,心却先虚起来。
“我觉得不像”他非常肯定地说。
看多了亦舒,总是最钦佩科学家,最爱慕工程师,毕竟文人都是无用的山水花鸟画,绣屏上看来够斯文也奢侈的,是富贵人家有腔调的好看。
看了悦目,赏心,然而总是隔膜着的,吃穿用度不从文化的根基里来,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实着心眼锻造的。
故此我一贯觉得,写诗,作画,从文,调曲,都不如科学来得迷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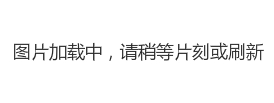
我爱看书,爱烹调,无不良嗜好,从小是老师最器重的好学生。
然而,我也喜欢匪帮,不看言情,单看武侠,小时候最敬仰李小龙。
也最爱开快车,把引擎哄得震天响,贪恋轰鸣声有烟火的流丽,但是时间更长,几乎能留香。
车也一定要开到120码,悬挂硬,像风颠雨恶,即便插脚红尘,一刹那的平地上青天。
当然也会飙车,又是N牌,总有一种不明事理的嚣张,我车技非常烂,然而又一味要求快,身后总是有不耐烦的鸣笛。
是一叠声抱怨性的长吁短叹。
而我却总莫名喜孜孜的,闲抛金弹落飞鸢,自觉十七人中最少年。
某次坐友人的车,为贪玩,一直别着另一辆杀气腾腾的改装车,把姜红色车里坐着的棕红色墨西哥人气得拉下车窗直爆粗。
我挑挑眉,看他竖起了滚圆的中指,一截不礼貌的腊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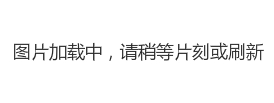
接下来的场景自然是很戏剧化的,在熙攘的街上飙着车,互别着,很有动物性的张牙舞爪。
这样当然愚蠢,然而太快乐了。
快乐到像黑色大丽花的穷途末路,是最喜不自禁的亡命天涯。
风咻咻地从明兰色的跑车上涌过,风翻暗浪的时候,人生也是不宁静的,随波逐浪到天涯也值得欢喜。
我又最爱听都市奇谈,听办公室里身段丰腴黑里俏的姐姐说他男朋友家昔日的风光,滴溜溜的内双清水眼宝石样熠熠。
她的男朋友也是叫X哥的,身材练得非常古希腊风,不知道忽然被谁从大理石堆里刻出来了这样一个人。
胳臂上盘了条黑龙,又是某省的散打冠军,是大痞子晚景从良,半世浪荡都无碍了。
听到得意处,忍不住和听评书样不住催,比羯鼓催花还急点。
故此,看《教父》的时候极度羡慕,江湖自然是险恶得了不得,但正因为这样的险恶,短短的太平才格外珍贵些,是玉里镶了金。
不过日子终究还是要四平八稳地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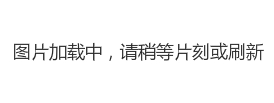
回国了,时差还未倒回来,天色黑了又白,日子流星样闪过,年末的日子像沙漏的余下几滴。节蓄着,反而汨汨地流走了。不如挥霍着点,也并没有分别。
更爱黏着姐姐玩,两个人躲在阁楼样的小房间里絮絮,午后的阳光细沙样把房间塞满了,空间小,更亲近。
像过年通宵挤被窝,手边有各色零嘴儿,反而还形容极小,但又自觉老了,虽然还不及相逢话旧,意极忘言。
自己在家坐不住,天稍亮了就信步往姐姐家里走。
整个人肚子里灌满了冲了奶粉的豆浆,走快些,就咣当作响,我一壁走一壁把脸躲在围巾里笑。
自觉是一匹英式矮脚马,虽然还没落日,万山寒,萧萧还。
国内的小区和南方公园的沃尔玛一样,已发展出自我进化,筑得极高,铜墙铁壁装饰着,粉墨登场。
也科技化得厉害,非得刷一刷卡才能进出。
连安保都穿着有勋级的制服,虽然并不合体,天又冷,有点瑟缩着,整个人都不太合时宜,是个阴沉着脸色的套中人。
湖边的天,连着水一并冻硬了,千年石髓似的,云又非常窄,瘦成一绺绺,像清泉石上流。
这位土塑扁方脸的安保脸色也是铁青,说话粗声大气,一壁追问着。
我一面接着电话,一面说,不知觉延续了说英文的习惯,把单元、幢、楼道给颠倒了。
他不耐烦地开了门,沉着脸色,态度非常不佳。
或者因为天气太冷了,把脸都浸得有些木了,我的笑容忽然冰屑样开裂了。
于是板正了脸,问他的工号,抱怨他再不改良态度,便投诉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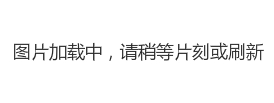
他的表情是几于愤怒的怀疑,很动物性的,很快拿手遮住了工牌。
他有庄稼汉的手,按在崭新的塑封白工卡上,徐唯辛的<工棚>里凭空而来的手,有劳作后的油腻和疲倦。
“是你没说清楚,投诉什么投诉”他重申,但是为着声音非常大,在我听来简直有些恶形恶状了。
被这样一激,我反而笑了,“好,那等你的领导来。”
他乌青一张脸孔,脸色空洞洞的,有一种留白的怨毒,“让你走就走”他催促着,又找来一个煤炭脸的安保怼着我。
更激发了我的斗志。
“我要投诉你们,我站在这,你也别走”我很镇定地说,虽然妈妈常说赤脚的不怕穿鞋的,不至于和底层人士计较。
但我的脾气到底还是惯坏了。
而且姐姐在电话里说,叫他们站在那,看谁敢走。
大家都看大话西游,嘴唇如一朵花开的紫霞,眼神比跳动的烛花更暧昧,悠悠说,“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,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,我只猜中了前头,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。”
我并没有看多少周星驰,他生得极清俊,性格也孤僻,在荧幕上费力耍宝,这种好笑有种披肝沥胆在里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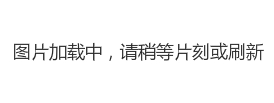
像那本冒名张爱玲的港派小说标题,《笑声泪痕》,看多了心酸。
然而很奇怪,我的英雄她穿着毛茸茸的黑衣服,刚修炼成人形的美貌墨玉猫儿精,切切地扑来护住我。
她还觉得我很小,其实我也受过磨砺,咽下委屈,然而她觉得我是她的妹妹,我没长大。
我看着她飞奔过来的模样,是宽幅旧电影的慢镜头。
丹凤眼气得滚圆,厚而圆的绛唇和樱珠一样鼓,我像是第一次发现她这样杏腮桃脸的好看,非常细地看。
这个女孩子,笑盈盈的时候甜得像刚剥了壳的荔枝,神情冷淡的时候又像欲雪的天,从小我和她一起长大,却很久没有好好看仔细她。
她来了就一叠声地数落安保。
安保变了颜色,抹土搽灰的庄稼汉的脸,服了软后意外有一种滞重的怨恨,是朽木雕的脸,风吹日晒后表情模糊了,只剩一点轮廓。
“是她自己说得不清楚,把顺序说倒了”他嘟哝着分辨,声音还是很响,然而是空心的,不硬气。
“这是你的职责,说话颠倒了如何”她很铿锵地说,伸长了脖子,像一只黑凤凰。
安保悻悻地,散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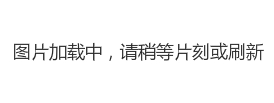
我忽然觉得这一切很荒谬。
我永远发脾气的不是地方,从来没有正确地逞能过。
进了电梯,她撑着手,散了头发,垂了头,极吃力地说,“宝贝,我头很疼,先别我说话”。
电梯里的淡蓝色数字悠悠浮起来,是晴天里阴阴的鬼火,我看着她的手指尖,鹅卵形的指甲盖桃花瓣似的。
为着用力,细而窄的手指上爆着青筋,抵着按钮的键。
我定格一样看着她的手,这双手直按到我心里。
到了家,姐姐就病倒了,“你先别理我,我一吵,头疼得神志不清了”,她躺倒在床上,白厚的被褥像一个茧虚虚裹住了她,她此刻非常脆弱,也像一个茧。
重重帘幕密遮灯,不仅能遮灯,也能遮日月。
现代化的窗帘的唯一好处,最盛夏的晴日也能变作雨夜。
我看着她,等她醒。
过了一段,她醒了。
神志还不太清明,说起了她的头疼病,已经愈发严重了,因为涉及到了左脑的诸多血管,无法开刀,连激素也只能缓解。
可是我姐姐又是最爱漂亮,糖果样储了一柜香薰蜡烛,第一时间到手最新款式的包,非常注意体态,弄花熏得舞衣香,是个不娇滴滴的美人。
她当然不愿吃激素,只能嗑止痛药,稍一动气就会疼一天。
我心里轰然一下,原来她病得这样重,却仍旧要为我强出头。
我说不出话来,然而脸颊却湿了。
去厕所看,她吐的止痛药软化成絮状的牛乳白,一朵一朵犹疑着的桃花水母,被湍湍的水冲走了。
我又折回床前,静静跪坐着扶着头哭了一会儿,棉麻质地的被褥吸了水,贴紧了脸上,又冷又薄,是某种欧洲式的白手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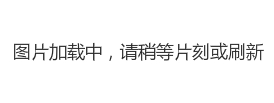
维系着贵族式的礼貌,感觉不出指尖和手掌。
我擦了擦脸,悄然去到了沙发上。
手指头冻得像块玉,镯子叮叮当当打在手腕上,几作金石之声,和朋友说了这件事,又说姐姐给气病了。
“都怪安保,不怪你,倘若我在,一定叫他满地找牙”他这样安慰,讨我开心。
是啊,买车时我蓦地悟到被坑了一笔,非常想投诉销售,以工会的停职迫使他退订金,然而爸爸远在国内,为了安全考量,逼着我忍了气,按兵不动。
当时我哭得岔了气,非常气恼。
“为什么我没有学泰拳的男朋友,身边又不认识会武功的青年才俊”我太恼怒了,腔调都变得无赖。
“其实我会和他硬杠,每天带一柄刀接你下班好了”他习惯了我的口不择言,只有无奈。
“有刀有枪都没用,我要是当大哥的女人就不会受这样的气了”我非常固执。
他很哑然。
然而这次,我却说,“这次是我错了,别打打杀杀了,成年人的江湖又不是刀光剑影”。
他反而诧异,“你不想当大哥的女人了?”
的确,从格林童话看到古龙,我没有为白马王子和骑士,霸道总裁抑或高富帅所折服过,因门槛太低了些,略平头整脸脸,身段气质做足姿态,就可以。
潜意识里,我一向渴望江湖气极重的大哥,是最现代化的游侠,是哥舒,横行青海夜带刀。
即便西屠石堡取紫袍,也非常金灿灿有辉光,因为传奇本身就短。
我有极度强烈的英雄情结,是很流俗的侠客精神,也并不港派,多点贾樟柯电影里那种百姓化的奸邪也没关系。
这很像某种图腾,隐约得几乎鬼影憧憧,是类似双鱼玉佩的引,引向找不到的地方。
我非常热衷于看《教父》,兽性被西装革履包裹住了,人性又被权谋给抑住了,是古井,也是暗涌。
看着非常激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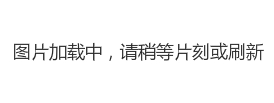
《教父》中,这个世界上最迷人的男性说,“你花时间和你的家人在一起吗?不照顾家人的男人,根本算不上是个男人”, 他也说,“你是我的兄长, 我爱你但我绝对不允许你做对不起家族的事——帮外人。”
能做到这一点的人,不拘男女,都是英豪,比千篇昌谷,万卷邺侯还更可爱。
晚上爸爸知道了这事,很冲动地要致电管物业的总经理,好叫那位安保当天就失业。
像是属河豚的爸爸,总是很轻易就爆炸。
这本来非常使我有安全感,然而他飙高了血压让妈妈软硬兼施量度数的时候,又让我记起爸爸已经廉颇老矣。
老却英雄似等闲,然而爸爸的脾气还很年轻,和我身边二十多岁要作大哥的男孩子们并无二致。
不过,我不再想当黑帮老大的女人了。
因为,原来我的江湖里早有一位侠女,她和风四娘一样,吃最辣的菜,喝最烈的酒,骑最快的马。
她也和像燕七一样护短,逞能,甚至有些外强中干。
当我怀念江湖的时候,就和她呆一会儿。
后记
祝欢欢大宝贝少生气,不要头疼,
永远是甜甜的,可爱女人。
作者:钱雪
作者:钱雪
相关热词搜索:女侠
上一篇:升魅提出情感幸福度公式决定两性关系走向
下一篇:科治好告诉你,分手之后如何正确疗伤
- 0

- 0

- 0

- 0

- 0

- 0

- 0

- 0

评论排行
频道总排行


